感谢资源与补丁的制作
游玩状态并非全线通关,可能存在文本谬误
文章存在大量引用,并参考了AI意见
图文导读
——要是能变成鸟就好了
八月九曰。夏天,正当时。
这种青春期少女常有的逃避性感伤,
竟在我临近二十岁时涌上心头。
这样的自己真是可怜、悲惨、可悲。
想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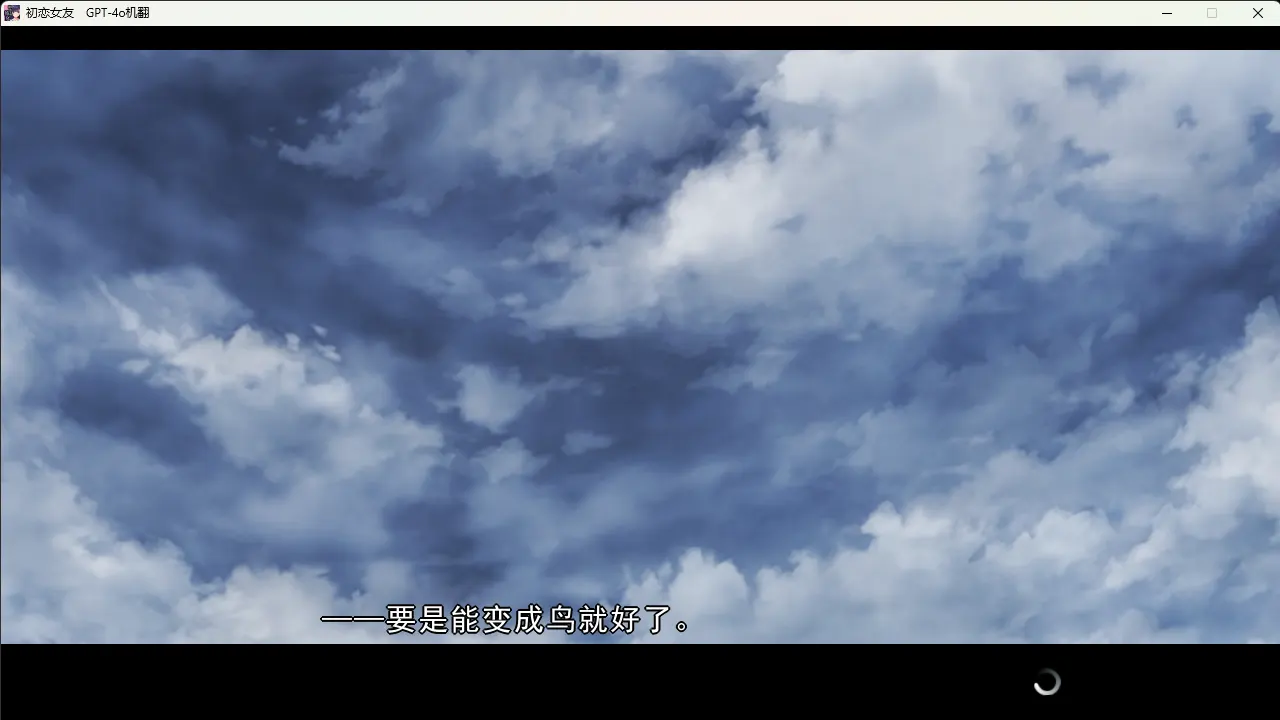 二十岁,其实正是一个非常多愁善感的年纪,我深刻能理解女主的感受。由于辍学过,那时我好像在读大一?甚至会感叹道:打出了BAD END,人生依旧继续着。
二十岁,其实正是一个非常多愁善感的年纪,我深刻能理解女主的感受。由于辍学过,那时我好像在读大一?甚至会感叹道:打出了BAD END,人生依旧继续着。
秋乃用“可怜、悲惨、可悲”进行自我攻击,她斥责自己没有感受悲伤的权力,连痛苦都是不合时宜、令人羞耻的。
母亲:「你也很忙吧。真是个勤快的孩子啊。」
秋乃:「我不就星期三才来吗。一周一次还不行吗。」
母亲:「打工很辛苦吧。不用勉强自己哦。」
秋乃:「这么说着,不来看你你还会生气呢。」
秋乃:「本来想买个苹果过来的。对不起,忘了。」
母亲:「别在意。你能来看我就很高兴了!」
母亲:「对不起啊。都是妈妈的错。」
秋乃:「说了没关系啦。我都听腻了。」
秋乃:「虽然是有点辛苦,但现在还能应付。真的别担心。」
母亲:「希望能早点出院啊。你也想早点回到大学吧。」
秋乃:「如果勉强出院,身体又会垮掉然后再回医院的。」
秋乃:「有时候不休息不行。对吧?」
母亲:「你是不是又瘦了?有好好吃饭吗?」
秋乃:「一直在打工,忙得连饿的感觉都没有。」
秋乃:「之前有点胖,现在刚刚好吧。」
母亲:「……」
秋乃:「啊,已经这个时间了。」
秋乃:「对不起,今天也有打工。妈妈,我会再来的。」
秋乃:「保重身体。」
母亲:「嗯,你也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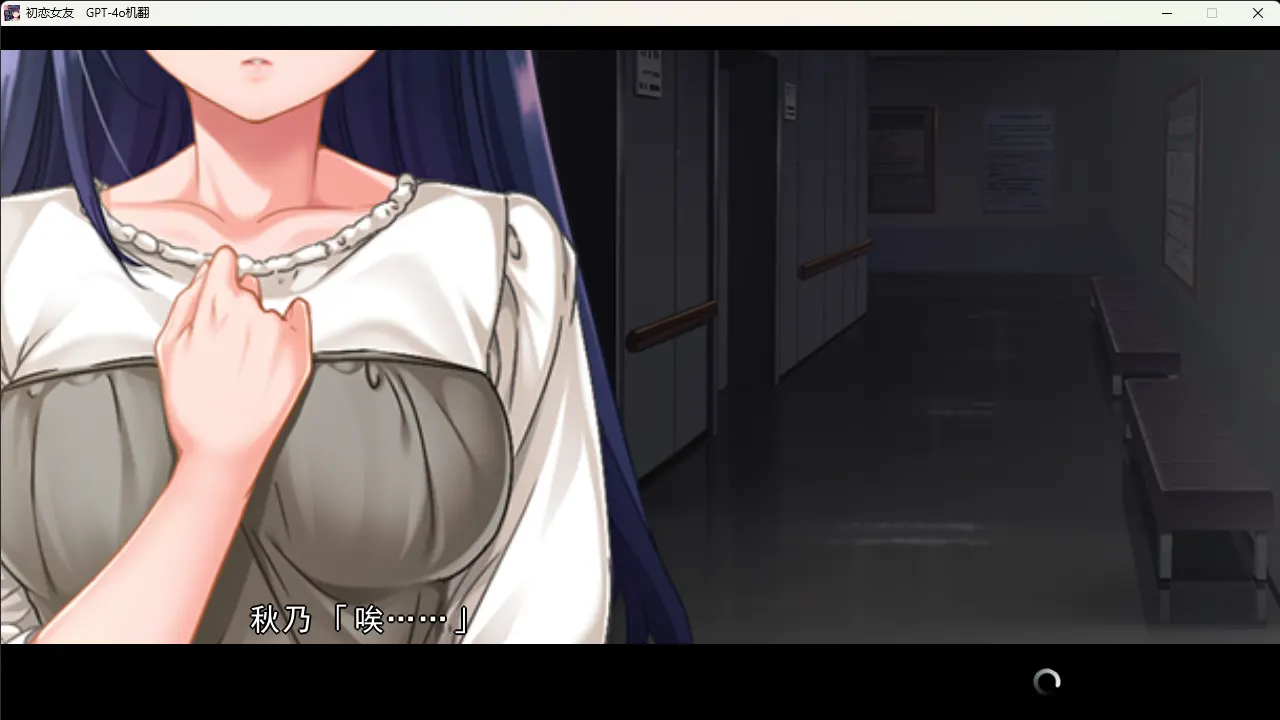 出门之后,少女悄然叹气。在母亲面前强撑的“一切还好”,表演结束后终究精疲力尽。
出门之后,少女悄然叹气。在母亲面前强撑的“一切还好”,表演结束后终究精疲力尽。
母亲反复的道歉,小心翼翼的关怀,她的愧疚,让秋乃的牺牲在情感上无法指责,痛苦无处宣泄。
秋乃
「………我回来了。」
深夜,回到空无一人的房间。
脱鞋踏进客厅的瞬间,便倒了下去——埋在洗好的衣物堆里。
能洗完衣服,却永远无力完成最后一步:将它们收进柜子。
太累了。
得吃点饭……从早上就什么都没吃。
可念头一转:少吃一顿,就能省下一点伙食费。
昨天交了拖欠的房租和居民税,钱包已经空了。
连给妈妈买探病苹果的钱,都舍不得花。
视线落在桌上——那堆熟悉的催促信。
居民税、年金、保险费、房子的债务。
昨天付掉一些,却连冰山一角都未动。
像抽掉一块将棋,整座高塔顷刻崩塌。
「啊,得洗澡。」
看了看钟,日期已经变了。
公共浴室早过了开放时间。
汗黏糊糊的,昨天也没洗吧?
可是…好困。
连衣服都没换,拉过玄关旁的棕色毯子,缩成一团。
想吃饭、想打扫、想洗澡…
结果还是困得睡着。
灯也没关,就钻进毛毯里。
毛毯的世界。只有我的世界。
没有催促电话,只有安静的黑暗。
安心、放松、心情平静。
好困啊。
要是早晨永远不来就好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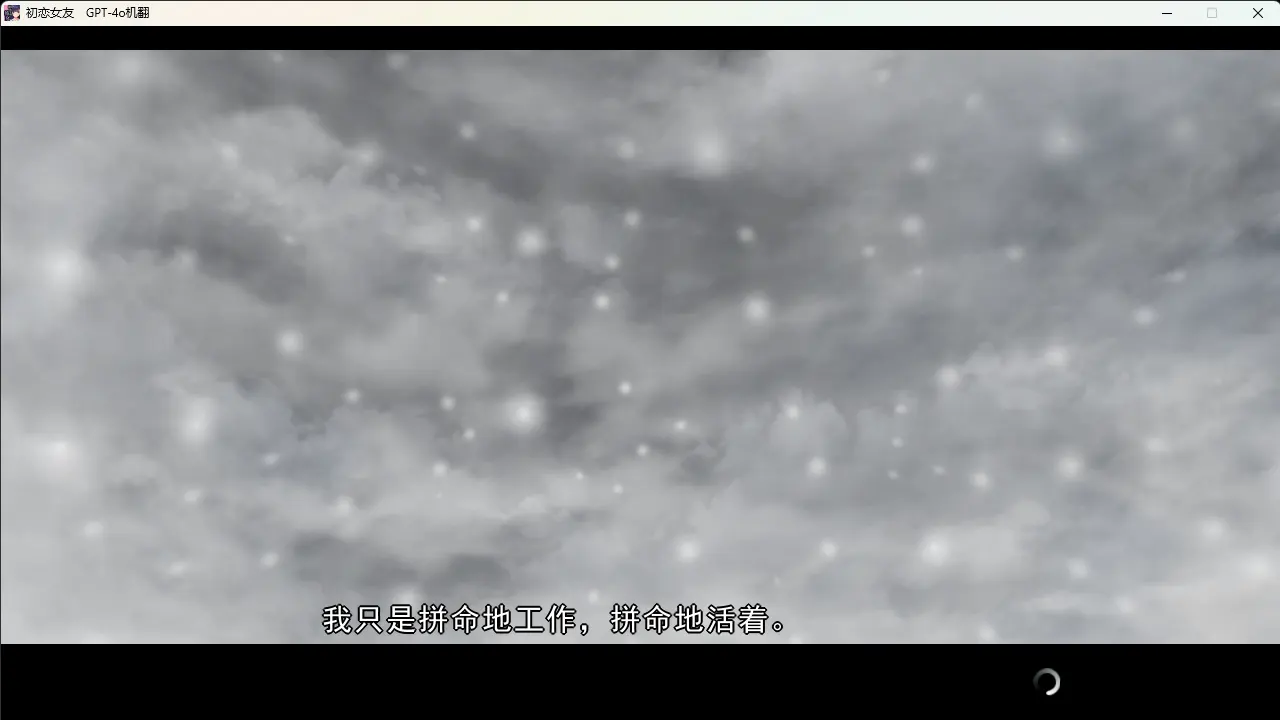 从“生活”,退化到“生存”,甚至“存在”都成问题。
从“生活”,退化到“生存”,甚至“存在”都成问题。
“吃饭、打扫、洗澡”,这本是维持一个人基本尊严与正常生活的三大支柱,相继崩塌:
- 从“得吃点饭”,到“算了…少吃一顿就能省下一点伙食费”。为了节省,一条百元小面包从午饭变成晚饭。
- “本该扔进垃圾桶的东西,满地都是”。她意识到“不打扫不行”,但她的自我已经在高压下被磨损到无法发出有效的行动指令。
- “日期已经变了”、“昨天是这样吧”、“上次休息是什么时候来着?”——她对时间的感知是混乱的,陷入了一种重复的、停滞的、令人疲惫的循环。家中没有浴室,附近浴室下班后早就不能用了,最终,她带着这种污浊感入睡。
当外部世界充满压迫时,人的精神会退行到最原始、最狭小的空间寻求安全感。她通过切断与外界的一切联系,精神上自我冻结,来获得虚假的片刻安宁。
旁边座位的一群讨论出游的大学生,与正在啃食廉价面包、忙于生计的秋乃形成同框,一记沉重的心理打击。

明明有那么多事情要做,最近怎么也早起不来了。
迟到的她心想,“真是的,上大学的时候从来没有这样过”。
大学,是她曾经拥有秩序和希望的象征; 但随后,这象征被挤压如山的账单淹没。
她又在绝望中悔恨,“果然,不该上什么大学啊”。
她开始习惯在客厅睡觉, 一遍又一遍翻阅着招聘杂志的兼职工作, 怀揣一个梦想:“想要尽快回到大学,我必须回去”, 借此重新振作精神。
这时,一个“月入三十万,每周两天,欢迎新人”的广告, 让她整个人都扑上去, 就像溺水者看到浮木时激动。
但看到是风俗广告,立马自我否定: 这是绝对不能做的事情。
像蚯蚓一样慢吞吞在榻榻米上爬,裹进了最喜欢的毛毯里
把头也裹住,就变成了一只棕色的小乌龟
睡觉的时候,可以忘却所有烦恼。
店中的兼职主妇闲聊间突然闻到一股臭臭的味道。
不禁抱怨,“刚才走过的店长忙的连澡都没洗吧,真是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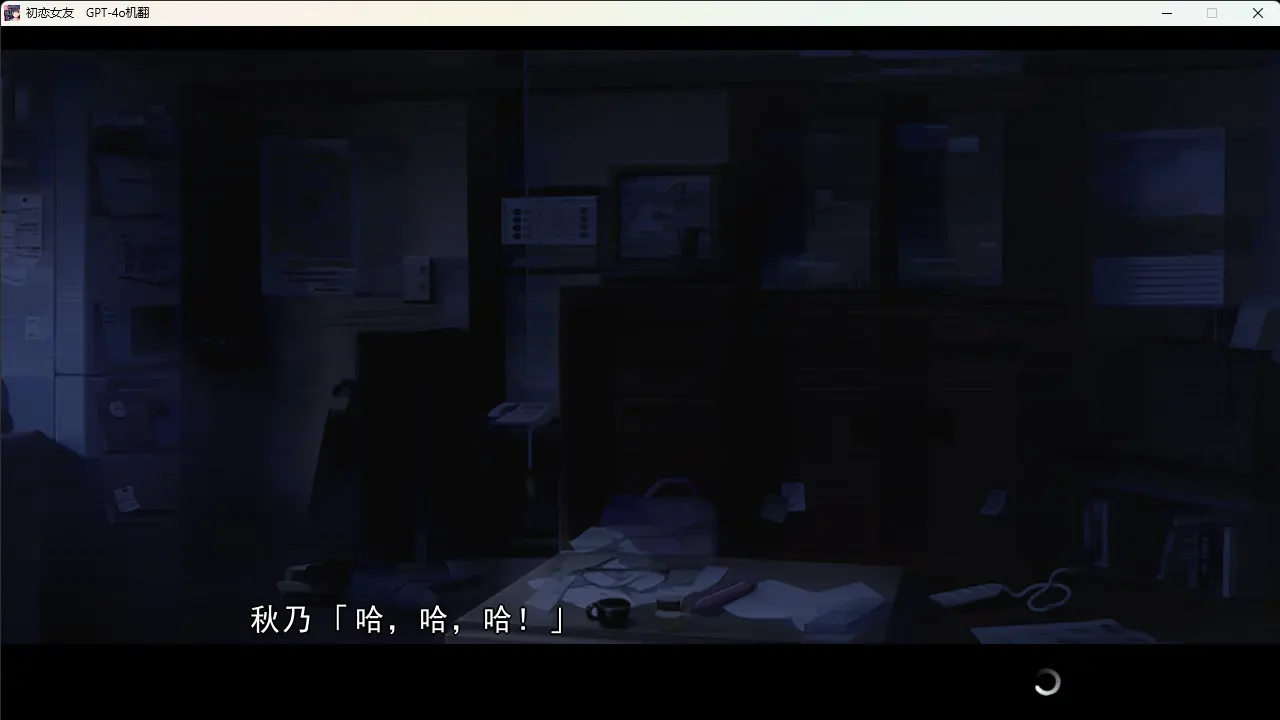 画面一转,她仓惶逃回昏暗的家
画面一转,她仓惶逃回昏暗的家
“洗澡,得洗个澡”
抄起钱包却发现空空如也
堵上自尊的她,委屈地呜咽起来
她本想向他人伸出援手,回想到公寓里的中年妇女的眼神,又立马自我否定
依赖别人,就是向人讨东西,是可耻卑鄙的行为
一旦真的被依赖,就会露出厌恶的表情逃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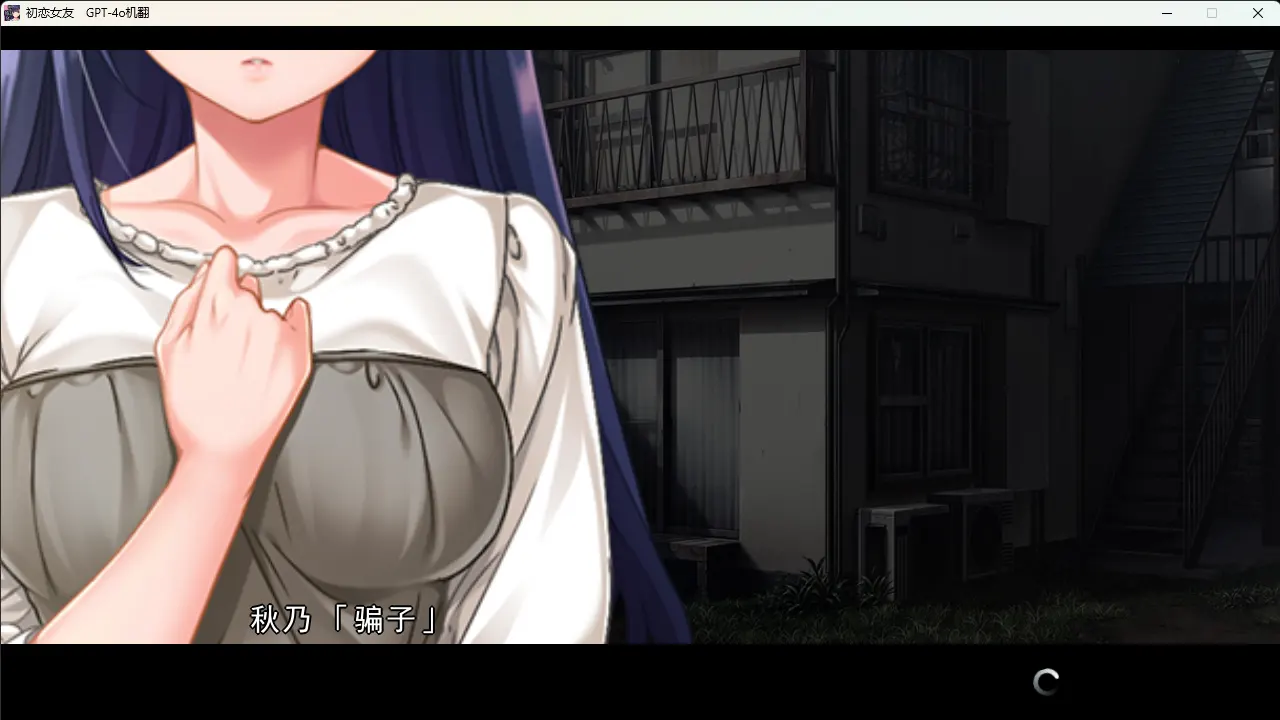 笑得次数少了
笑得次数少了
哭的次数多了
自言自语也多了起来
“……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呢?”
“肚子,好饿啊”
一天不吃饭
可以省下500日元
虽然可以冒险复学
每月借几十万
但这其实就是增加债务
此刻,那条风俗广告,又像致命的恶魔一样映入眼帘
 打开窗户,是低的伸手就能碰到的平坦天空
打开窗户,是低的伸手就能碰到的平坦天空
即使能飞,也会马上撞上天花板掉下来的吧
《经济景气的时候,有些女生一个月就能积攒下三百万》
《前台的小弟在上专门学校,他还是个学生,还有上短期大学的女生,文章说不是风俗经验者超过三成了吗?》
《提供免费住宿,甚至安排好普通公司的文件,完全合法,形式上在那边工作》
《我们是泡泡浴店,是否做本番由女孩决定,在法律上,本番在任何店都是禁止的》
第一次去的风俗店,比想象中普通的多,也不像在粗暴对待女性
相反,他们向对待宝物一样维护我们,我的认知一小时内完全改变了
 但少了反感也是事实,为了复学的最短路径
但少了反感也是事实,为了复学的最短路径

探视母亲,秋乃问她一个人抚养自己的历程,她说:
越是辛苦的时候,就越努力,不依靠任何人,一直这样
最终能依靠的,只有自己
加油吧,你是我引以为傲的女儿
 少女怀揣梦想,从悬崖走向了深渊————
少女怀揣梦想,从悬崖走向了深渊————
后文将以第一视角展开,大量引用并整合原文片段
我紧紧咬住颤抖的嘴唇
强行睁大眼睛,忍住快要流出的眼泪
勉强忍耐住了,开始初次培训
一边摩擦身体,一边质问自己,我这是在干什么呢
完全没有现实感
以坚定的觉悟继续动作
想逃跑,想回家
但停下来又能怎样呢
 拿到初次三万的培训费,视线转上桌上一大堆烦人的催缴单,竟然这么轻松就解决了
拿到初次三万的培训费,视线转上桌上一大堆烦人的催缴单,竟然这么轻松就解决了
这不是做梦吧
现在还可以回头,但辞职后又能做什么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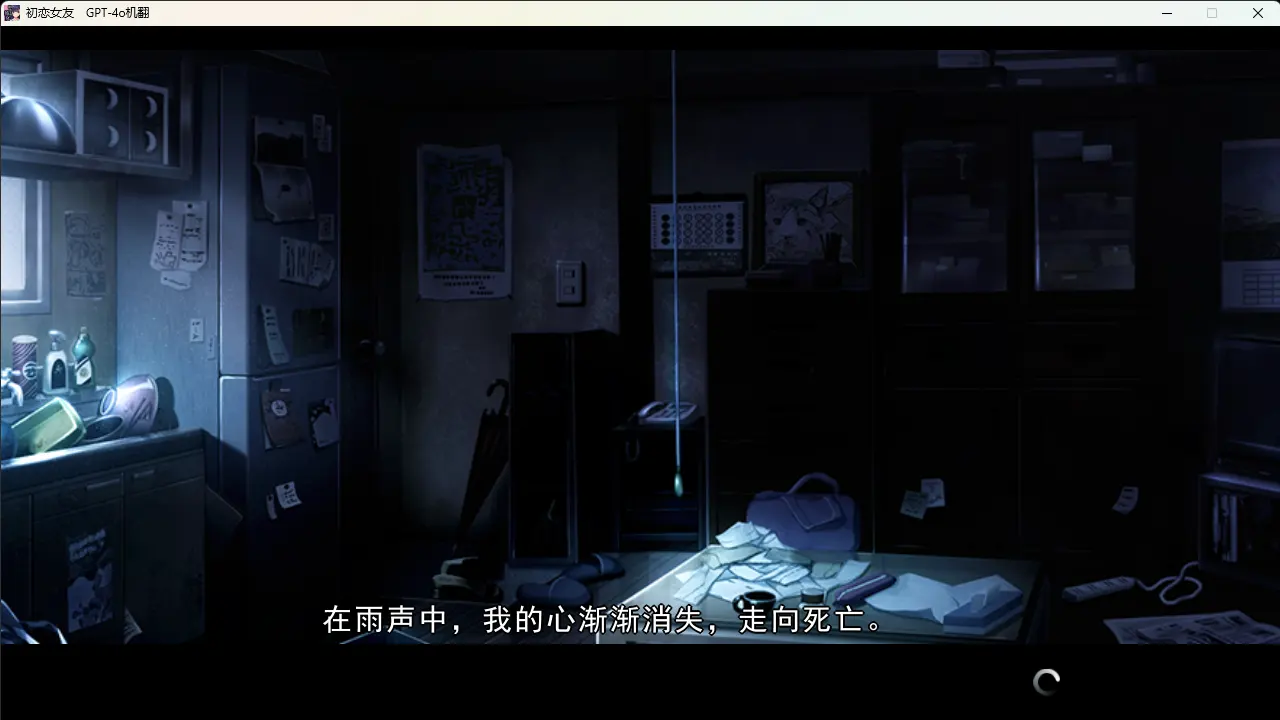
「我是秋乃,虽然是新人,请多关照。」
(眼前映入的是少年瞪大的瞳孔)
「雪宫桑?」
「高木君,是你吗」
(这是两人的再次相遇)
(而此刻的高木仅仅是一个学园生活的印象符号)
(名字不记得了,只记得姓氏)
(怀揣着不安,舍弃掉少女的羞耻心,开始服务第一位客人)
(本来笃定决心,我就是个风俗女郎——)
(但面对以前的男同学,羞耻心却总在行动前涌上心头)
「今天谢谢你了,如果能再次指名我,我会很高兴的」
(少年非常高兴地收下联络地址)
「我很担心你,如果可以的话,我想帮你」
虽然感受到他热烈的气息
可我不免困惑
为什么你要这么拼命?只是一个许久不见的老同学而已
时薪一万五千,今天只接待了一个客人
两个人就是两倍
三个人就是三倍
如果傍晚前一直工作到下班——
十五万?家庭餐厅打工一个月的工资,只需要一晚上,也许用不了一年就能全部还清
瘫倒在床上,眼前看到甩到脸上的白皙手臂
这是一只人偶的手,玩具的手,像是怪异的棍子,即便用菜刀在手腕切一刀,也不会有什么流出来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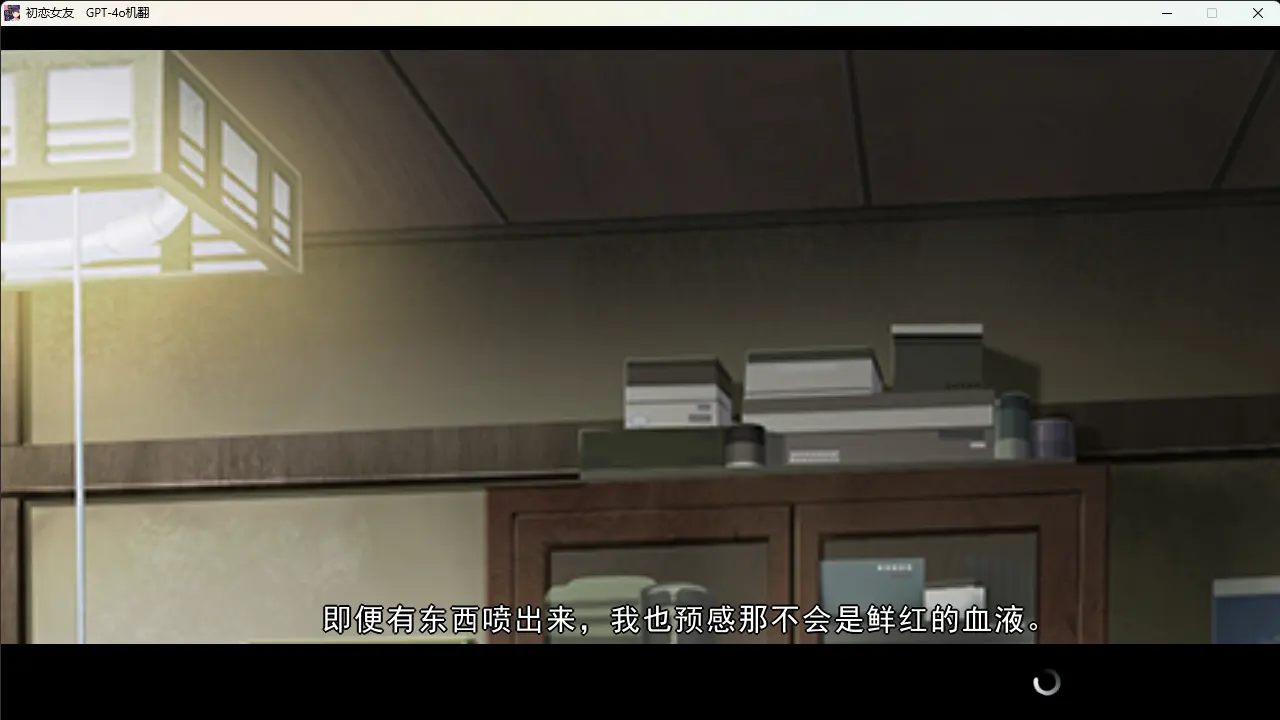 那天晚上,我久违的做了个梦
那天晚上,我久违的做了个梦
夏天,蝉鸣声,汗湿的手心,教室
一切都那么美丽而闪耀
那是我完美的青春时代
真想再回到那个时候啊
(在餐厅再次见面之后,两人持续着无关痛痒的对话)
「雪宫,你是大学生吧?我也在附近上大学,还有那个经常和我在一起的家伙」
(心脏仿佛被揪住,想笑出来却做不到)
(抬不起头来)
 我什么会这么肮脏呢?
我什么会这么肮脏呢?
他那顺风顺水的人生真是让人羡慕
嫉妒别人的幸福,我真是个坏孩子
“为什么要在那种地方工作?”
罪恶感和自我厌恶几乎要压垮我的胸膛
“为什么想知道我的事?只是好奇吗?”
躲闪的目光,扭捏的态度,脸红却拼命想说些什么
我大概知道了,难道是——
我不禁对自己涌起的感情感到羞愧
抱有不切实际的期待,我到底要保持那个美好的自己到什么时候呢?
我不过是个卑劣身份的女人
 像逃跑似的,对自己说,我是风俗女
像逃跑似的,对自己说,我是风俗女
依赖别人是罪过,向人乞求是可耻的行为

少年的表白是如此热烈
曾经的我跟在别人后面走很不自在
可如今,他的背影看起来好大
我踩着高木的脚印,追随他的步伐
 他发自内心放松的表情
他发自内心放松的表情
和高中那时一样
心中涌起一丝温暖
只是一时冲动的邀约
看着他那滑稽点头的样子,我不禁笑了出来
有多久了呢?
已经很久没有这样无所顾忌的笑了
抬头看向天空,是如此的温柔

(明明从事肮脏的职业)
(战战兢兢地吐露心声)
(迎面是他直率的眼神,他接受了这样的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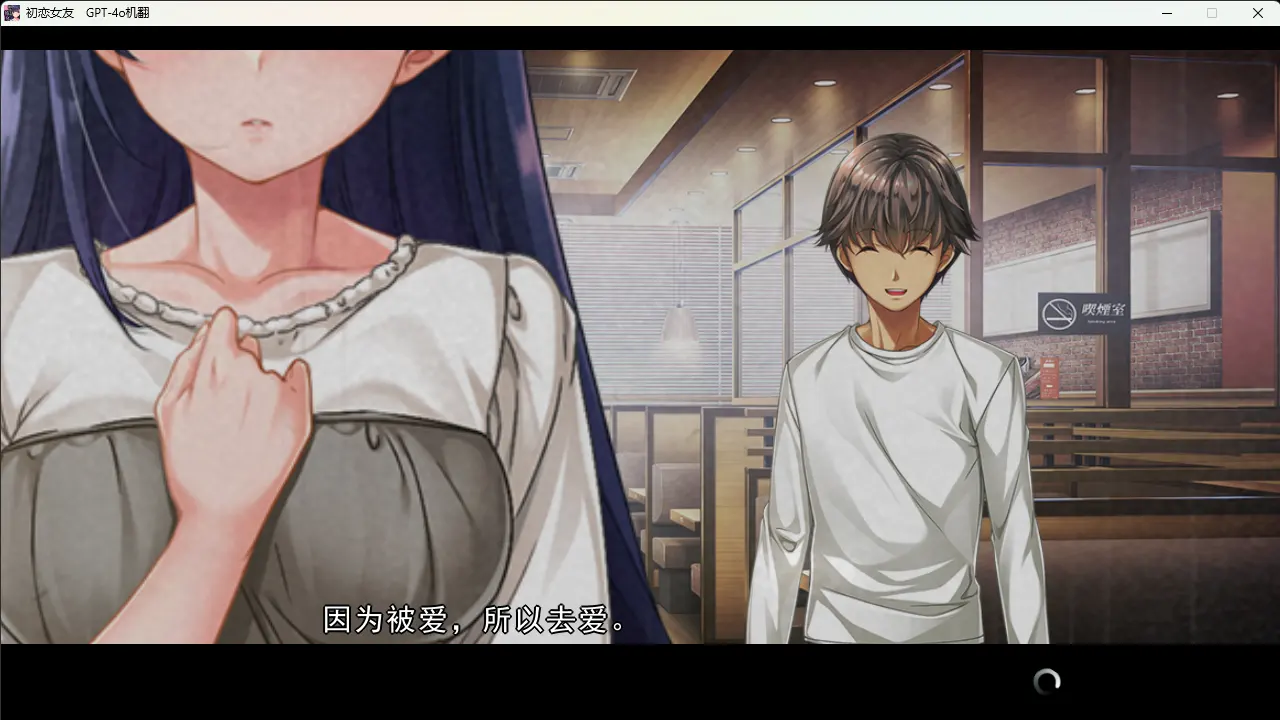 因为被爱,所以去爱
因为被爱,所以去爱
对现在的我来说,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
扑进他的怀中,让我回忆起遥远的过去
那是我遗忘的东西,这是世界上最令人安心的地方。
少女决定将一切献给少年——
如梦般的宁静世界终于变得炽热
寄宿着灵魂的心脏像是催促般敲响着钟声
连夜晚辉映下的深蓝虹膜,如今也能看到
羞耻感却带来了安慰
那是我早已磨损殆尽,消失不见的东西
浮现的疑问让灵魂渴求答案
达到顶点的紧张感让世界变得狭小
温热的盛夏之手轻轻拂过
胸口的寒冷与无助, 那时我回归本真的证明
对于污秽的我来说,这种羞耻的幸福是奢侈的
是我的意识在模糊吗?
还是说,包含热气的空气本身在模糊?
 像我这样的人,真的能做到接受另一个人吗?
像我这样的人,真的能做到接受另一个人吗?
这一年来,我深刻体会到了,我是个软弱,胆小,卑鄙的人
想相信自己不是一个人,但还是害怕
他那过于温柔的温柔,让人心生爱意
在这个广阔的世界上,有多少人能像他这样对我温柔呢?
在六七十亿的人群中,对我来说,只有他一个
如果没有遇到他,可能会因为孤独的寂寞和人生的艰辛,把自己卖给一个连名字都不知道的人。
此刻的我无疑是个幸福的女孩。
夏日的昏暗中,一道光划过他的脸颊
最终,还是让他哭了
我真是个坏孩子
他是否注意到了那滴泪?
他不知道,只有我知道——他的秘密。
除了我,还有你在,真的好温暖
啊,幸福——
第一次遇到同一天生日的人,名字的由来和我一样,在我最痛苦时出现,救了我
“现在的我,无法接受你的告白,对不起,我觉得自己没有资格站在你身旁”
我不能给这个深爱的人带来麻烦,无论是金钱方面,还是名誉方面
“总有一天,不知道是什么时候”
“我会辞去这个工作,回归普通女孩的生活”
“到那时——”
 啊,那该多幸福啊
啊,那该多幸福啊
光是想象,就让心如此温暖
他只是轻轻触碰了下我的嘴唇,很快就分开了
其实可以更长一点的嘛
如果可以任性一点的话,希望他能紧紧抱住我,然后亲吻
如果可能的话,抛开世俗的眼光,顺其自然一直到天亮
我深深吸入他留下的气息,想着已经离开的他
果然,还是应该请求他留下来过夜的

一场精心策划的自我毁灭
秋乃的形象,并非简单的“受害者”或“堕落者”
而是一个在结构性暴力下,自我认知被系统性摧毁,最终主动参与并完成这一毁灭过程的悲剧灵魂。
她的沉沦之路,可以概括为以下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自我存在的否定——“我无权痛苦”
病态的内化攻击
她在二十岁这个多愁善感的年纪,却用“可怜、悲惨、可悲”来斥责自己的感受。这并非谦虚,而是一种深刻的自我否定。她内化了外界的压力(社会规训、家庭期待),认为自己的痛苦是“不合时宜”的,是一种软弱和耻辱。这使得她的痛苦无法向外宣泄,只能转向内部,不断进行自我攻击,为后续的精神崩溃埋下了伏笔。
被绑架的牺牲
在与母亲的互动中,母亲的愧疚(“都是妈妈的错”)成为秋乃无法挣脱的枷锁。她的牺牲因为母亲的痛苦而变得“无法指责”,这剥夺了她抱怨和退缩的正当性,迫使她必须独自咽下所有苦水,在母亲面前维持“一切还好”的表演。
第二阶段:生存尊严的剥离——“我无需为人”
基本生存维度的坍塌
从“生活”退化到“生存”。吃饭、打扫、洗澡——这些构成人之为人的基本尊严与秩序感的活动,在她这里逐一瓦解。她通过自我矮化(将消瘦视为“刚刚好”)和经济理性(不吃饭是为了省钱)来说服自己接受这种非人状态。
时间的停滞与空间的退行
她对时间的混乱感知(“日期已经变了”)和放弃卧室、在客厅睡觉的习惯,象征着她已从正常的生活轨道中脱落。那个“毛毯的世界”和“乌龟”的意象,是她精神上的绝对退行——通过将自己封闭在最小、最原始的空间里,来模拟一种虚假的安全感,本质上是精神的自我冻结。
第三阶段:道德防线的侵蚀——“我无路可走”
希望即陷阱
与大学生的对比,让她看清了自己失去的世界。而招聘杂志的桥段是关键的转折点。她对“月入三十万”的广告本能地扑上去,是求生欲的体现;而迅速意识到这是风俗广告后的自我否定(“这是绝对不能做的事情”),是她道德底线最后的、也是无力的挣扎。
认知的扭曲与重构
当她最终踏入风俗店,发现“他们像对待宝物一样维护我们”时,她的认知在一小时内被改变了。这是最令人胆寒的情节之一。她不是在认可这份工作,而是在极端压力下启动了心理防御机制,通过接受环境提供的“合理化”解释(“普通”、“合法形式”),来缓解认知失调带来的巨大痛苦,为接下来的行为扫清心理障碍。
第四阶段:灵魂的割裂与献祭——“我无我,唯有他”
在拿到第一笔收入后,她看着自己的手臂觉得是“一只人偶的手”。这表明她已经开始将自我的主体与从事性工作的身体进行切割。她通过将自己物化,来逃避行为本身带来的道德审判和心理创伤。
高木的出现,是她沉沦过程中最复杂的一环。
羞耻感的回归
面对故人,她那早已被压抑的羞耻心猛然回归,这说明她内在的“好女孩”人格并未完全死去。
对“纯洁”的贪婪
高木代表的纯洁学园生活,是她最渴望却最不可及的东西。他的爱越真诚、越热烈,就越映照出她的“肮脏”,加剧她的自我厌恶(“我为什么会这么肮脏呢?”)。
爱作为新的麻醉剂
她将高木的爱视为唯一的救赎,扑进他的怀中是“回忆起遥远的过去”。然而,这种爱在此时更像是一种情感的依赖和新的麻醉。她通过将自己“献给”少年,来完成一种仪式——仿佛通过他的纯洁,可以洗涤自己的污秽。
幸福的奢侈与自我资格的剥夺:
她感受到幸福,却立刻认为这对于“污秽的我来说”是“奢侈的”。她拒绝他的告白,认为自己“没有资格”。这表明,外部沉沦已然内化为深刻的自我否定。她为自己描绘了一个“辞去工作,回归普通”的未来图景,这个幻想本身是她活下去的动力,但也成了一个永远悬浮在前方、无法触及的海市蜃楼。她独自品味着那个短暂的吻和离去的他,幸福与巨大的悲凉交织——她获得了片刻的温暖,却更深地坠入了无法与这温暖相匹配的自我认知的深渊里。
失衡的天平——救赎幻象与结构囚笼
男主高木,“太过温柔的温柔”
主观能动性几乎为零。他的温柔,在故事的语境下,已然异化成一种消极的、无力的共犯。
他将秋乃视为不容玷污的白月光,这本身就是一种物化。
他爱的或许不是真实的、复杂的、浸满污泥的秋乃,而是他记忆中那个纯洁的符号.
这种仰望,使得他不敢,也无力去触碰她真实的痛苦。
秋乃说等辞去风俗工作再交往,高木回答“我会一直等着”,
秋乃希望更长久的亲吻,他却“只是轻轻触碰了下她的嘴唇”,
秋乃渴望抛开世俗,一直到天亮,又担心他被传出不好的谣言,让他离开,他只会摆手“我不介意”,
表面是尊重,实则是情感上的怯懦和行动上的缺席。
他无法提供一个能将她从沼泽中拉出来的、强有力的现实方案。
他是一个顺风顺水的大学生,他的世界规则是努力、等待和遵守道德。
而秋乃所处的世界,是道德失序、需要即刻的生存智慧的。
他用自己世界的规则去应对秋乃的危机,这本身就是一种错位和不匹配,注定是无效的。
女主秋乃,“因为被爱,所以去爱”
历经生活的磨砺,秋乃早已变成了一个胆小、自卑,有严重心理问题的女孩。
家庭和社会环境训斥她,“依赖别人,就是向人讨东西,是可耻卑鄙的行为”。
“必须做个好孩子的我不能喊出声,但希望有人能伸出援手”,她热烈的盼望着他人的拯救,他人的美好和温暖。
她纯洁、脆弱、柔软,却置身于在漆黑的沼泽中。没有足够的能量无法对抗外在黑暗的侵蚀。
纯洁无法成为力量,反而成了被吞噬的弱点。黑暗不会因她的纯洁而退散,只会更快地将其染黑。
在长期的情感与物质双重匮乏下,她像一个真空的容器,任何一点温暖都会让她贪婪地吸附。
高木的出现,对她而言不是平等的爱情,而是濒死之人抓住的氧气面罩。
她的爱,混杂着绝境中的感恩、依赖和抓住救命稻草的迫切。
她希望有人能伸出援手,与现实中高木的无力形成了最残酷的反差。
她需要的不是一个等待的王子,而是一个能劈开荆棘的战士。
但高木不是,也做不到。
当“等待”,成为最残酷的刑罚
“辞去工作再交往”。这个约定,是一个美丽的泡沫。
高木没有经济能力。仅凭秋乃自己,在那样一个高薪但扭曲的行业中,偿还巨额债务并全身而退,难度如同登天。行业的惯性、来钱的容易会成为一种新的枷锁。即便她未来能离开,这段经历带来的心理创伤和污点也将伴随她一生。高木那句我不介意显得如此苍白,因为社会会介意,她内心的自我审判更会介意。
等待这个行为本身,就将她钉在了不洁净的当下,而将幸福的可能无限期推迟,这本就是一种缓慢的精神凌迟。
他们的关系从开始就注定是一场无望的守望。
高木是岸上那个焦急却不会游泳的人,只能看着秋乃在泥沼中下沉。他的爱是真实的,但他的无力也是真实的。而秋乃,在渴求一个她明知不存在的强大拯救者的同时,也清醒地意识到自己的沉沦是换取生存的唯一筹码。
在冰冷的结构性现实面前,它毫不留情地揭露了,仅凭个人情感的,纯粹的爱、纯粹的温柔,是多么的苍白无力。它摧毁的不是一个女孩的身体,而是她对于爱能拯救一切这份最后幻想的信念。
